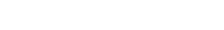车窗外的黄土高原正化作水墨氤氲的背景,手机信号在沟壑间时隐时现。前方即将进入秦岭山脉。我的指尖无意识划过玻璃,仿佛要触碰那些被岁月焐热的褶皱。

隧道口的光亮突然吞没车厢,风在钢铁管道里发出低沉的呜咽。这不是我第一次穿越秦岭,却依然会下意识屏住呼吸。黑暗中,关于这座山的记忆碎片如山泉般涌出:地理书说它是南北分野的界碑,寒流在此绕道,暖湿气流在此驻足;历史课本里,秦汉的明月曾照亮它的峰峦,隋唐的驼铃曾漫过它的垭口。
但对陕西人而言,秦岭从来不是冰冷的地理符号。爷爷总说,秦岭是咱的“靠山”。儿时在关中平原的麦浪里奔跑,抬头望见的那道青灰脊梁,就是天地间最安稳的坐标。春天看山桃花将沟壑染成粉白,夏天听暴雨裹着雷声从山那边滚来,秋天捡被山风捎来的野栗子,冬天望着雪线爬上山尖——那是秦岭在叮嘱:该回家囤白菜、腌腊汁肉了。
黑暗仍在蔓延,仿佛要拉人坠入更久远的时光。或许千年前,某个赶考的书生也曾在这样的山道上跋涉,松涛如浪,长安城里的母亲叮咛犹在耳畔;或许百年前,某队驮货的脚夫曾倚着岩壁歇脚,烟袋锅的火星与头顶星光遥相呼应。秦岭默默收容所有南来北往的脚步,将乡愁酿成山涧清泉,把牵挂长成崖边古柏。

忽然有细碎的光从前方涌来,像是谁悄悄掀开了厚重的幕布。风里漾起湿润的草木香,光线变得温柔,不再是西北高原那种直白的锋芒,而是被树叶筛过的、暖洋洋的斑驳。
当列车冲出最后一个隧道,渭河谷地正铺展在阳光下。远处的村庄顶着淡青色炊烟,空气里浮动着熟悉的泥土腥气。此刻终于懂得,秦岭哪里只是一座山?它是陕西人血脉里的坐标,是无论走多远,一抬头就能认出的故乡方向;是无论过多久,一呼吸就能嗅到的乡愁浓度。
列车继续向前,秦岭的影子渐渐落在身后,却又像从未远离。就像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印记,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你清晰地知道:到家了。(浩海煤化:刘佳萌)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