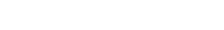一场寒潮袭来,气温骤降,我的故乡东北更是接连暴雪。生活在西北,经年所见的雪皆是轻柔飘逸,而记忆里故乡的雪,大多犹如鹅毛状,伴着刀锋般凛冽的寒风,漫天卷地落下来。不多时,屋顶上、村落里、田野间就被这漫天的白雪包围覆盖,在这静谧之间,小城被装扮成一个童话的世界。

故乡的雪是母亲缝制的棉衣。儿时的记忆里,“秋老虎”一过,母亲拿起针线笸箩、一把剪刀,开始大制作,一家子大大小小的七八口人的棉衣,薄的厚的各一身。先将旧的棉袄拆解,里子和面子浆洗一遍,棉絮则重新打理,一点点絮成巴掌大的圆片备用,小孩个子长得快,就在胳膊、裤腿拼接一截花布,铺满棉絮,再一针一线精心缝制成衣。母亲做的棉衣总是合体舒适,精致大方,穿起来略显笨拙,却比如今任何一套名牌羽绒服都要保暖,也许是因为里面是母亲满满的爱。
故乡的雪是热炕头的饭菜。寒冷的清晨,父亲忙着清理院子和路上的积雪,母亲早起提提喀喀地忙活,生上锅连炕,烧水做饭时,经过一夜早已凉了的炕被烧得热腾腾、暖烘烘的。熬上一大锅的白米粥,煮几颗腌制的咸鸭蛋,切上一碗咸菜丝,拌上几滴香油,一切准备妥当,母亲便大着嗓门喊我和姐姐起来。洗漱后,一家人围坐在热乎乎的炕桌前,吃着母亲从锅里盛出热气腾腾的饭菜。我迫不及待先抢过一个咸鸭蛋,在桌子上敲破空的一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一下红油就冒出来了,一咬满嘴流油,再配上可口的清粥小菜,整个味蕾都被熨烫舒服,身体仿佛彻底清醒且充满活力。
故乡的雪是孩童天真的笑脸。吃过早饭,穿上母亲做的新棉衣,孩子们就不再怕冷,几个小伙伴步行上学,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或是沿着车辙印打滑,追逐着,嬉戏着,向着学校的方向。下课铃声一响,孩子们蜂拥而出,在操场欢快地嬉闹,打雪仗,堆雪人,滚雪球,在冰面上打陀螺,溜冰,大家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个个脸蛋冻得通红,满头大汗,手上甚至皲裂,可却仍旧笑的没有一点烦恼。
又是一年寒冬,回首那些曾经的点滴碎片,愿如故乡的雪般宁静与祥和,念流年的暧,轻拾着过往的岁月记忆……(炼焦二车间:张晓秋)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