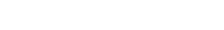我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据说有百十多年了。
在我有记忆起,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记得生产队那会儿,树上挂着一个铜铃,每天上工前,队长摇动铃绳,人们听铃声,不约而同的来到大树下,队长分配活儿后,都各拿着工具去劳动。
春天,农活少点,妇女的活儿就除麦地的草,打个药什么的?男人则是修地或收拾准备夏播的田,那时候,土地上的都是土粪,主要队上养的牲口粪便,年龄大的人则是翻粪的轻活。
夏收夏播是一年最忙的时候,那时所有活儿都是人干,时间要一个多月,先麦子收到场里,打成垛,防止淋雨。“麦到场里,秋争晌”是当时流行语,麦收后要种玉米,玉米的生长主要积温,种的过迟,积温不够,影响成熟,下茬种麦。因此那时都先收麦后种玉米,玉米种完后再碾场。

碾场是用人最多的活儿。天一亮,人们开始摊场,把麦子均匀的放在场里,并不停的翻晒,那时我这里半机械电碌,其实就是电机通过简单传动装置,但效率不错,一天也能碾三四十亩地的麦子,麦碾完后,开始启场,启场男女老少齐参与,妇女们主要是用杈把麦粒和麦杆分开,弄成一堆一堆,男人把麦杆积成麦积供队里牲口食用,年纪大的人把麦粒带麦壳推成若干个麦堆,等待扬场,孩子则在场里戏喜玩耍。午后,一阵风来,人们开始扬场,扬场是技术活儿,都是队里“能人”的专利,当第一堆麦扬时,人们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
麦子颗粒归仓,那时候麦子上缴公粮,剩下麦子根据劳力情况,人口情况,按一定比例分给社员,这就是一年的主粮,我们这里水利条件好,产量也不错,上缴国库的粮食也多些。分给社员的也不少,在当时也算远近闻名“富裕村”。麦场的活要持继一个多月。
麦场接近尾声,秋管秋收慢慢开始,施肥,除草,浇水。施肥多是农家土肥,用人力车,一车一车拉到地里,那时唯一的化学肥料是氨水。氨水要跟水上,效果不错,庄稼也不错。玉米收获后,我们这里上缴国库以小麦为主,玉米直接分给了社员,留少一部分给牲口做饲料。那时人们生活虽苦点,但很快乐。
秋收秋播结束,严冬己来临,人们播下希望麦种,等着来年的丰收,一年又一年,一晃几十年,儿时记忆又浮现眼。
真想回到从前,回到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快乐的童年。
老槐树,沥尽沧桑屹然站在那里,记录着历史,记录着那段时间里人们生活。(炼焦二车间 赵仲强)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