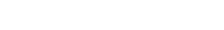咸涩的海风裹着夏意撞上面庞,我牵着七岁女儿的手,四岁儿子像小藤萝般攀着我的裤腰,踏上刘公岛码头。
甲午战争纪念馆如一艘青铜巨舰泊在山海间,劈开百年雾霭,十五米高的邓世昌铜像目光如刃,穿透历史的尘烟,恰好落向仰起的两张小脸——姐姐的眼睛亮得像星子,弟弟的睫毛忽闪着,正用指尖戳裤袋里的贝壳。

馆内光线幽沉如深海。玻璃柜中,济远舰的铁锚裹着沉沙,锈迹爬满筋骨。女儿踮起脚,指尖轻轻点着展柜:“爸爸,这些褐色的…是他们流的血吗?”她的问题撞进我眼底——陈列柜另一侧,金州曲氏十口的蜡像凝固在1894年的冬夜,妇孺相携立在井沿,裙裾被阴风吹得翻卷。我蹲下身,将姐弟拢在臂弯:“这口井里,沉的是不愿被践踏的尊严。”
转过回廊,黄海海战的3D影像正翻涌。漫天炮火撕裂屏幕,定远舰燃成赤焰,“亚洲第一舰”的钢板在火中扭曲。光绪帝的挽联悬在硝烟里:“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女儿的目光钉在邓世昌决绝的侧脸上,忽然拽我衣角:“爸爸,他们的船比日本的大,为什么会输?”弟弟被爆炸声惊得缩起脖子,小手攥住我的手腕,却没哭,只是把脸埋进我臂弯,从指缝里偷偷张望。
我带他们走到展柜前。弹孔密布的北洋军衣残片旁,一枚怀表的指针永远停在15:30——那是致远舰沉没的时刻。另一侧玻璃柜里,《马关条约》的复制品泛着冷光,“李鸿章”三字的墨迹在展灯下像一道血痕。“你们看,”我指着怀表,“北洋水师的水兵能把炮术练到‘十发九中’,德国克虏伯大炮的射程能覆盖整个黄海。可他们不知道,炮弹里装的是沙子,火药库里堆的是掺了土的硝石。
转角处,那尊跪地的北洋士兵铜像攫住了我们的目光。他单膝陷进泥土,断枪拄地,左手死死捂着胸膛——青铜的指节暴起,仿佛还攥着未说出口的不甘。女儿松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过去,伸出温热的小手,轻轻覆在青铜手背上。
叔叔,她的声音像一片落在水面的花瓣,“你们的炮弹里有沙子,是不是因为…有人没好好工作?”海风穿过回廊,卷着她的话撞在青铜上。弟弟蹭到姐姐身边,踮脚望着那尊雕像,忽然也伸出手,像在确认他的温度。
归航的渡轮劈开碧波,船尾的红旗猎猎翻卷,像一簇烧在海面上的火。一群海鸥从浪尖腾起,绕着船舷盘旋,翅尖掠过红旗时,像是在与某种精神击掌。女儿摊开那只触碰过青铜的手,任海风拂过掌心:“爸爸,你看那些白鸟,是不是像叔叔们?”我望着那群在霞光里穿梭的精灵,陷入沉思——百年前沉在海底的,是冰冷的钢铁;百年后翱翔的,是不死的魂灵。它们掠过的每一寸海疆,都在诉说一个真理:器物的锋芒需要制度的淬火,技术的先进离不开精神的锻造。就像一家企业,再精密的设备,若没有严丝合缝的流程;再优秀的团队,若没有表里如一的坚守,终究是沙上建塔。
暮色漫上来时,刘公岛成了水墨剪影,岛巅的邓世昌铜像却愈发清晰,像一团烧不熄的火。海风掀起我的衣角,吹乱姐弟的发梢。我望着他们映着霞光的侧影,忽然想起那尊跪地士兵的眼睛——百年前,他的目光里是不甘的暗涌;此刻,两个孩子的眼睛里,有星子在跳。这跨越百年的握手,从冰凉的青铜到温热的小手,从历史的伤痕到未来的承诺,原来最锋利的传承,从来不是仇恨,而是清醒的自省;最珍贵的守护,从来不是重复,而是超越的勇气。
海天相接处,夕阳沉落,新的桅杆正在升起。而甲板上,两双小小的手,已经触摸过历史的脉搏——那曾让一个民族折戟的痛,终将在新一代的掌心,淬炼成更坚韧的光。
(黄陵煤化工:邱利军)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