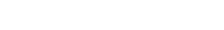在时代的褶皱里初见
徐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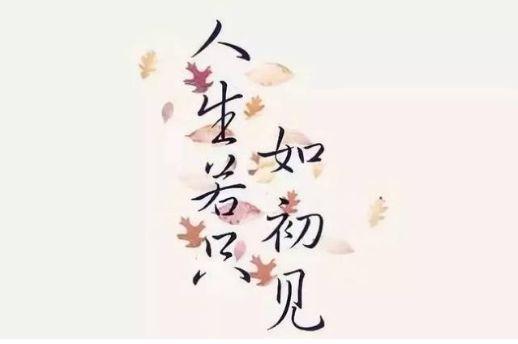
她原不过是想过好这一生。
起初,她只是江南烟雨里一抹伶仃的影子,像旧式宅院墙角悄然生长的青苔,静默而卑微。后来,她遇见了吴天白——那个满口新思想的年轻人,眼里燃着她看不懂的火。她仰慕他,像仰慕一册她读不懂的书,便跟着他漂洋过海,去了日本。那时的她,尚不知“革命”二字如何书写,只隐约觉得,这世道是要变的。
革命是什么?是吴天白深夜伏案时抖落的烟灰,是留学生集会时压低的议论,是藏在衣箱底下的油印传单。菽红不懂这些,她只是默默地煮饭、浆洗衣衫、在异国的街角开一间小小的杂货铺,用算盘珠子一粒一粒地数着生计。她从未觉得自己是革命者,可革命却像一场无声的梅雨,渐渐浸透她的裙角。
后来,她怀了梁乡的孩子。那是个雨夜,梁乡的枪抵在她的脊背上,像一截冰冷的铁。她蜷缩在榻上,想起吴天白曾说:“新世界的女子,当有挣脱枷锁的勇气。”可那一刻,她只感到一种钝重的痛——原来枷锁从来不是能轻易挣脱的,它长在血肉里。
孩子出生后,她给他取名“吴不顾”。吴天白说,这名字好,有破釜沉舟的决绝。她却低头笑了笑,心想:这名字是给孩子的,也是给自己的。
做母亲后的菽红,身上忽然生出一股柔韧的狠劲。她依旧温言细语,可眼神里多了些东西——像江南水乡的芦苇,风来时伏低,风过后又挺直。吴天白要刺杀梁乡,她死死拦住他:“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这话说出口,她自己都怔了怔。原来恨与生存之间,还隔着这样一道模糊的线。
吴天白带回阿霞,那个眉眼鲜亮的姑娘,满口都是“同志”“理想”。菽红站在柜台后,看着他们并肩而立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自己从来不是谁的同志,只是他们革命路上偶然歇脚的驿站。那夜,她收拾了细软,抱着孩子离开,像多年前离开故乡时一样安静。再后来,她遇见了杨凯之。他比吴天白沉默,却会在寒冬里为她焐热一碗甜酒酿。她在他眼里,终于不再是“吴天白的女人”或“梁乡孩子的母亲”,而只是菽红——一个会为晚樱落泪的普通女子。
那段日子短得像一场梦,杨凯之死在某个清晨,血染透了她缝补过的长衫。她没哭,只是将他的衣冠埋在院角的梨树下。来年春天,梨花开得惨白,风一吹,便扑簌簌地落,像一场小小的雪。晚年时,有人问菽红可曾后悔。她摇摇头,望着檐下滴落的雨:“我这辈子,就像这雨水——原想顺着瓦沟安安稳稳流到地上,偏叫风吹得东倒西歪。”可她又笑了笑,“但终究是落到了土里。”
她始终不觉得自己是革命者。可历史何曾在意过这些?时代的巨轮碾过时,从不分辨谁主动投身,谁被动裹挟。她只是在那道褶皱里,活成了自己的样子——温柔地反抗,沉默地坚韧,像一株从砖缝里挣出的野草。
人生若如初见,她或许仍会选择跟着吴天白上那艘船。不是为革命,只为在洪流里,看清自己究竟能活成何种模样。(党群工作部)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