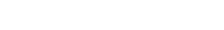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时,我总能看见他后颈那截白刺目的头发。印象里他的背是笔挺的,可如今驼成了张满弓,弯腰捡锄头时,衣角会先蹭到泥土地,像只疲倦的老雁,翅膀上驮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当我奔赴甘肃工作时,他默默地帮我整理行囊,阳光斜斜穿过窗户,在他的眼角犁出的深沟里注满阴影。我忽然发现,他的手指已蜷曲如老树枝桠,可当他抬头嗔怪我“笨手笨脚”时,眼里又突然跳出年轻时的光,像灶膛里未熄的火星。
他的热心肠总让我“头疼”。村里大爷家水管爆了,深更半夜拍门,他披着棉袄就去修;邻居家电线短路,家里停电,他风风火火的就出门了。我劝他“少管闲事”,他却蹲在家门口,掸着烟灰说“乡里乡亲的,搭把手怎么了?农闲时别人蹲墙根下棋,他却在院子里整理杂物,把碎砖块码得整整齐齐。下雨天不能下地,他就蹲在屋檐下修理农具,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是他生活韵味。
记忆翻涌,想起叛逆期的自己,总觉得喉咙发紧。那时我嫌他古板,嫌他唠叨,嫌他不懂我的“诗和远方”。他让我好好学习,我偏要躲在屋里看小说。有次吵架,他气得摔了我的笔记本,我哭着喊“你根本不爱我”,却没看见他转身时,手在门框上握出的白印。后来我去上大学,他送我到学校后,把装着学费的信封塞给我,说“在外面别委屈自己”,声音哑得像含着沙。我回头时,看见他站在站台边,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像根孤单的电线杆,却依然倔强地挺着。
如今远离家乡工作的我,才读懂那些藏在唠叨里的牵挂,那些藏在“小气”里的深情,也更加想念他的唠叨。父亲老了,背更驼了,头发更白了,可他依然会在我回家时,提前把我爱吃的菜炒好,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依然会在电话里说“别担心我,我好着呢”,却又悄悄让母亲叮嘱我“少熬夜”。那日傍晚,我们在院子里散步,他指着金黄的麦田说:“等收了这季麦子,给你攒着买辆车。”我看着他鬓角的白霜,磨穿鞋底的旧布鞋,忽然很想抱抱这个一辈子都在为家人操心的老人。
晚风掠过田野,带来熟悉的泥土芬芳,恍惚间又回到儿时。那时他背着我走过田埂,宽厚的脊背是我最安心的港湾。
父亲的爱,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藏在每一分“修修补补”里的节俭,藏在每一次“多管闲事”里的善良,藏在每一回“闲不下来”里的牵挂。他像一棵老槐树,枝叶渐渐稀疏,却依然用斑驳的树影,为我们遮风挡雨。
暮色渐浓,父亲的烟圈袅袅升腾,消散在晚风里。我多希望时光能走慢些,再慢些,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把那些没说出口的“对不起”和“我爱你”,慢慢酿成他喜欢的旱烟味,陪着他,走过一个又一个温暖的黄昏。(浩海煤化:杨俊)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