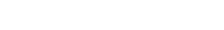墙上的日历翻了厚厚的一叠,门前邻居家的婶婶刚从县城里买回来的瓜子糖正往小娃娃们的口袋里装,藏在婶婶身后的小鬼趁着不注意,在她的身后扔了一个摔炮,婶婶顿时花容失色,追着小鬼跑了老长一截,追上后在屁股后面踢了几脚,还给了些带酒的巧克力糖果,就这样年如期而至。
小时候家里连着锅的烧炕特别暖和。一个土炕,接纳着爷爷疲惫的鼾声和奶奶收音机里凌晨的报点声,也滋养着我儿时大灰狼、所有鬼怪的梦,情景大概是长耳朵、大眼睛、尾巴翘到天上、流着哈喇子的大灰狼,专吃不听话的小孩;要么就是不用走路,可以飞起来,穿着一身红衣的女鬼,专门抓爱哭的小娃,梦着梦着,就惊醒了。窗外的光穿过窗帘跟冷风一起进来,屋里也变冷了,奶奶的收音机里报时声响了起来,热炕是前半夜热烫,后半夜变凉,裹着被子的我便不由自主的蜷缩起来,鸡还没叫,大人陆陆续续起来,准备着初一早上要吃的饺子。
屋后院畔柴垛落了雪,结了冰,填进灶洞只冒烟不起焰。爸爸使劲拉的着风箱,妈妈则用水瓢敲打着结了冰的陶瓷水瓮,灶火的火点不着,爸爸趴在灶口用吹火筒吹,青烟熏得眼泪汪汪,伴随着哐当哐当的风箱声,火总算着了,妈妈端着昨天晚上包好的饺子在一旁准备着,大铁锅里面的水烧的咕咚咕咚的响,妈妈一边喊着我说:“新年的第一天可不敢睡懒觉,这样这一年都是大懒虫”,一边把饺子扔到锅里煮,奶奶则在另一个锅里烧着要浇饺子的臊子汤,汤里有黄花、木耳、蒜苗、豆腐、胡萝卜、肉等不下十几样的配菜,到了汤滚得咕咚咕咚的时候,撒上一把韭菜,妈妈的饺子也就放到了跟前,浇上汤,再调点陕西人最爱吃的油泼辣子,忍不住馋的我准备一尝美味的时候,被爸爸打了一下“给爷爷端去,拜年!”。

那时候没有炉子,最佳的取暖方式是烧热炕,早起的爷爷正在炕边抽着他最爱的汗烟,看着我端着饭说:“快给爷,别把汤撒到身上了,弄脏了新衣服”,爷爷好像过年永远都是那件藏青的呢子大衣,他从口袋里掏了20块钱给我说:“过新年了,一定要好好学习,拿钱买点书,别光顾了嘴了”可能和大多数小朋友一样,都是耳旁风。下午就买了好多零食和玩具,以及一些画片,读书到后来也是家里最落后的一个。吃罢了饭,就出门找伙伴们去玩,和大多数乡俗一样,初一除非家里有丧葬事其余的也就不讲究拜年,男孩子就去各家门口捡那些没有燃尽的烧炮,用纸条引燃扣在碗里,比赛看谁的碗飞的最高,女孩子就臭美的比拼看谁的过年衣服漂亮,而最后都是拿着压岁钱去了商店买了自己心里惦记了一年的玩具。过了初一到了初二就要开始拿着烟酒看丈人,走姨家,看姑家,领的压岁钱便被爸妈以学费为理由保管了起来,年味也就慢慢的淡了。
小时候从过了腊八开始就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盼过年,也是因为爱年的热闹和不用学习疯狂玩耍的喜悦、大年初一的浇汤饺子和一家人闲坐在一起说着一年来的收获与烦恼,有爷爷的叹息声,奶奶的唠叨声,几个兄弟姐妹打趣声......
在摇曳的灯光中,温暖人间的烟火气也大概不过如此。
现在我到了而立之年 ,成了家,有了孩子,而对于年更多的是回忆,那些童年记忆中的年味也随着微信、视频电话等通过手里的手机发生了变化,大年初一的饺子也因为奶奶身体年迈,母亲离世也没有了当时的滋味,手机微信里的红包虽然数量较以前翻了几十倍但是却成了没有了温度的流通工具,爷爷烟斗里的烟火也随着一堆黄土,埋在了他最爱的那片果园地里,点不着的灶火也变便成了通了天然气锅灶,热炕当然也因为环保问题铺上了电热毯,时代在不断的进步,生活也在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变化着,而小时候熟悉的年味,也成了打麻将、唱K、拍抖音的最佳消遣方式。

细细琢磨,其实年也未变,只是我们生活的条件和观念发生了改变;变的是时代投影在春节的景象改变,而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现在我们对节日的庆祝方式也会成为我们孩子最怀念的样子,你看她正一脸天真的问我:“妈妈,什么是年啊!”,我现在要就要过年”。
而年,让我理解的就是团圆,就是可以包容所有的温暖人间的烟火,就是万象更新,迎接更多希望的起点。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