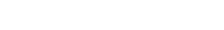家乡的年俗是从扫舍开始的。
小时侯,每到年跟前,最想逃避但却逃避不了的就是扫舍了。想起一大早要从暖和的被窝起来,要去搬瓶瓶罐罐,还要擦玻璃,我刚强撑睁开的眼,瞬间又想回到梦想。
最终还是没强坳过母亲。扫舍的时候,母亲总要选一个晴朗暖和的日子,她早早招呼全家人吃过早饭,给我和姐姐换上旧衣服,帮我们俩用围巾将头包严实,一家老小齐上阵。先将屋里的盆盆罐罐铺的盖的全部搬到院子中央,揭掉炕上芦蓆,把睡了一年压得平展展,烤得焦黄的麦草秸打扫干净,然后仔细地掏炕眼里的草木灰,最后再往一根长棍上的顶头绑上扫帚,从屋顶的蜘蛛网、灰尘等清扫干净。
掏灰是扫舍中最脏的活儿,母亲生怕呛着我们,常常由她一人去干。她先用长长的炕耙一下一下把积攒了一年的灰勾出来,再用木掀板小心地揽进拌笼。一时间尘土纷飞,大团的烟尘罩住了母亲,待装满一笼子后,母亲才唤我和姐姐近前,拿上炕耙抬进后院倒在粪堆上。

这时父亲早准备了一个大铁盆,将白土一块一块放进去,提起水桶倒入满满的清水,只听见 咝咝咝”地响声,白墡土像饥渴的牛儿饮水,一会功夫酥软松散,一股清爽的泥香味扑鼻而至。父亲又将几根高粱穗子绑在丈把长的竹竿顶端。刚掏完灰的母亲也不休息,紧接着便开始扫墙。她挥动竹竿,舞动着胳膊,高处,低处,明处,暗处,角角落落挂扫一遍,然后蘸上酥好的泥浆水,往墙上一下一下拍打,偶尔还要横着抹一抹,生怕有遗露的地方。母亲头仰得久了,难免脖子有点酸困,父亲便适时地递上一杯热茶,叮嘱母亲歇一歇。母亲接过茶,仰头大口大口的一鼓气喝完,然后干得越发起劲了。一个上午下来,母亲累得满头大汗,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水,只能看见两个眼珠在闪动着……
母亲稍微喘口气,又重新铺炕蓆。她先用泥水将炕面抹洗一遍,糊住漏烟的缝隙,提前烧热的土炕瞬间热气腾腾。待炕面干燥后,将晾晒了一中午白亮亮金灿灿的麦草铺上去,均匀地摊平。父亲用一根细细的棍子将芦蓆仔细地拍打一遍,弹尽尘土,卷成筒状扛进屋子,母亲站在炕上接住,两人小心地放到炕的一侧,松手后芦席就自然地舒展开来,平平整整恰到好处。
晚上,一家人躺在铺盖一新的土炕上,暖和和,软绵绵,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惬意。忙了一天的母亲又开始在厨房忙活……
农家的年关就在这样的劳碌中渐行渐近。也正因这样的辛劳,使我过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小家庭的温馨,更重要地是身体力行地体会到了父母养家的艰难。扫舍,扫去的不仅是灰尘,也扫去了旧的陋习和过去的不快。
新年近了,新的生活也从扫舍这一天开始启程。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