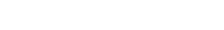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了,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夏雨里的入夜,黑暗中无限放大的雨声陪我走完了王琦瑶的一生。这个典型的却不怎么光明,清醒却自持的上海女儿,弄堂的狭隘、流言的环绕,飞过低矮屋檐无言注视着她的鸽子,每一个细小的笔触勾勒出的形象,真实、悲凉,无以言表。《长恨歌》,王安忆先生用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4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世界对王琦瑶这个住在逼仄弄堂里的女孩,尤其是自持有美貌,美且自知的女儿来说,身边的流言哄着你做一个“花好月圆,长聚不散”的梦,按耐不住的内心打开了闺阁的房门,走向了舞台的中心。“上海小姐”第三名的名头,
灯红酒绿、眼花缭乱,她也终于有了现在聚光灯下的骄傲。“李主任”的资本,程先生的爱情,比起自己的野心,她更知道怎么选择。这是1948年的上海。“李主任”死后,王琦瑶暂避邬桥,江南水乡的宁静没有打动她,安静的生活也不是她要的。回到改天换日后的上海,50年代的王琦瑶,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改变不了的依旧是上海女儿的方式,小而精致的点心、时尚独特的旗袍,甚至交友的聚会也略带点沙龙的味道。身边围绕的人,或许是旧人的改变,或许是新人的加入,王琦瑶永远是得体的。意外而来的女儿是她人生的继续,作为过来人的母亲,能教会女儿的是对时尚的镇定把握去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守着旧潮流,对着新世界。女儿离开家后,守着寂寞,甚至想用所有的积蓄换来一段不合时宜的陪伴,终被拒绝。直至最后,那个雕花的,繁华而精致的,装着一箱子金条,是王琦瑶最后的希望的木盒,却成为了她亡命的匕首。最后的那瞬间,她会不会觉得,四十年前人生开始的那个片场,已经遇见了最后的样子?“不耐和消沉相继而来,希望也是挣扎的希望,它是闺阁里的苍凉暮年。心都要老了,做人还像没开始似的。”
博尔赫斯说:时间的广场可以容纳一切,时间之外的一切。王琦瑶的人生是勇敢的,虽然不那么光明,勇敢的做选择,承担一切,我无法设身处地的评价王琦瑶的一切。可奇怪的是,作者描绘的王琦瑶的人生的每个阶段,似乎都有另外一种人生在跟她做比较。少年时期,逼仄的弄堂阁楼,对她漠不关心的妈妈,蒋莉丽家的独院,凡事都听女儿意见的蒋莉丽的妈妈;王琦瑶以为的富庶生活,随着“李主任”飞机的坠毁,一无是处,王琦瑶的未来虚无缥缈,与此同时,吴佩珍随家人离开战乱的上海;新时代固守着旧方式的王琦瑶和迈入人民阵营、意志高涨的蒋莉丽;讨厌粗鄙的家人,临死却是家人给她最后温暖的蒋莉丽和死于非命、孤身一人的王琦瑶……说不清楚到底是谁的人生更幸运,不可复制的时间撕碎了所有的美好。千疮百孔的旗袍掩盖不住的是王琦瑶的坚守,却平添了眼角的皱纹。作者用嘴细腻的笔触,好像慢镜头般的,一帧一帧略过雕花的矮铁门、临街二楼的窗户、院里的夹竹桃、盘桓的鸽群,定格在背阴的窗边,拉开窗帘,王琦瑶定目遥望着两街阁楼中间透出的那点光,想了好久……弄堂口的电车声、梧桐树上的蝉鸣、卖甜食的梆子声,都没能打断她……她在想什么呢?
徒留一声叹息。(醇氨车间 高玉倩)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