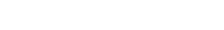夏日的兰州,骄阳为奔腾的黄河披上粼粼金甲。甘肃省博物馆入口处,九岁的女儿踩着脚下滚烫的地砖不停张望,检票队伍如长龙缓缓蠕动,她踮起脚尖数着前面的人数,发梢被风掀起又落下,每一秒等待都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甘博之旅。不同于初次走马观花的懵懂,这次她提前半个月就翻烂了我做的文物图册,在作业本上临摹了几遍马踏飞燕的剪影——虽然每次都把飞燕画成了胖麻雀。
通过闸机,我们直奔二楼展厅中央,东汉铜奔马以颠覆物理常识的姿态悬浮于空中。仔细观看青铜马的笑容,颇有一种“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的韵味。讲解员微笑着俯身:“你看它腾空的瞬间——右后蹄踏飞燕,左前蹄向前跨越,另外两蹄向后蹬踏,形成四点支撑。这是极速奔跑时肌肉的爆发力凝固成了永恒。”光影流转间,青铜的脉络仿佛有血液奔涌,三十三公斤的铜块被汉代工匠注入了对抗地心引力的灵魂。
转入丝绸之路展厅,女儿拉着我快步走向角落展柜:“找到了!”“像不像冰雪女王用的杯子?”女儿高兴地说到。莲花形玻璃托盏在射灯下流转着诡异的光芒,钴蓝色基座上绽放着十二瓣莲花,仿佛刚刚从莫高窟壁画里的宝池采摘而来。我打开提前准备的资料书:“这是七百年前元代工匠从波斯学来的钠钙玻璃工艺,制作了佛教圣花造型的茶具哦。”女儿睁大眼睛,幻想自己是一粒沙漠中的石英,在商队皮囊里颠簸千里,最终在工匠的吹管中绽放成莲。
彩陶展厅入口处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前,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工用简练笔触勾勒出神秘的人面鱼纹,那双穿越五千年的眼睛正与我们对视。“妈妈,她有点像童话里的美人鱼。”女儿轻声说。但讲解员告诉她:“这是中华始祖伏羲氏“人首蛇身”图腾的最早实物佐证。”她忽然举起手腕上的儿童手表,对着展柜“咔嚓”一声。照片显示的表盘背景里,彩陶瓶的鲵鱼纹与她最爱的小美人鱼贴纸奇妙地重叠在一起。“你看!都是鱼尾巴!”她兴奋地比较着新石器时代的彩绘与现代卡通贴纸,跨越五千年的审美在此刻完成了童趣的共鸣。
离馆时夕阳西斜,我们捧着鲵鱼纹样的雪糕坐在博物馆台阶上。女儿忽然说:“妈妈,下次我们带爸爸一起来第三次好不好?”我看着她被冰淇淋染蓝的嘴角,忽然懂得——最好的教育不是刻意的熏陶,而是共同经历时那些鲜活的瞬间。当五千年的文明穿过时光长廊,最终落在孩子品尝甜品的笑脸上,这便是文化血脉最生动的延续。(富平分公司:张晓秋)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