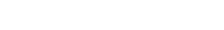轻微的夜风卷着秋的气息,从敞开的窗缝溜进来,带着草木褪去燥热后的清爽,拂在胳膊上,是恰到好处的凉。凌晨翻了个身,凉意顺着被角钻进来,迷迷糊糊中摸索着扯过薄被盖上——这早晚间钻心的凉,终于让我猛然惊觉:原来立秋已至。
立秋从不是一场骤然降临的寒凉。是正午的蝉鸣不再连片聒噪,像被风剪碎了似的,漏出些疏朗的间隙;是市场摊位上的瓜果沉了糖心,咬下去时,甜意顺着舌尖往胃里钻得更深;是檐角的风铃被风拂过,晃出 叮铃 一声轻响,像岁月在时光册上轻轻翻过一页。夏的热闹还在树梢挂着,秋的沉静已立在门外,带着晒足了夏日的暖香,轻轻叩响窗棂。
老话讲“立秋十天遍地黄”,田垄里的谷穗沉了头,人也得借着这节气补回精气神,“贴秋膘”的习俗便由此而来。记忆里,老宅门前那棵老枣树,总在立秋后把青黄的果子催得红透半边。这时奶奶便会扛出那根长竹竿,铁钩在竿头闪着光。她握着竹竿的手布满老茧,手腕轻轻一旋,铁钩便勾住枣子的蒂,“啪嗒”一声,红透的枣子裹着夕阳的金辉坠下来,滚进事先铺好的麻袋里。

我总吵着要试,奶奶笑着把竹竿递过来。可那竹竿在我手里像生了根,怎么使劲都拧不动,急得鼻尖冒汗时猛地一拽,竟把一根细枝丫折了下来。青黄的枣子落了一地,奶奶心疼地抚着断枝:“傻孩子,摘枣要用巧劲,立秋的树得轻着待,不然来年就不肯结果喽。”
傍晚的厨房总飘着肉香,炖得酥烂的排骨,拌着糖霜的瓜果,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竹椅晃悠悠的,说的都是对秋收的盼。枣子的甜混着饭菜香,连晚风都带着暖。
工作后,离家远了,每天都匆匆忙忙的,直到夜风吹过打了个寒颤,才想起翻日历——立秋已过了好几天。马路上行色匆匆,没人会留意枣子红了没有。可总在这样的时刻,想起老枣树下的黄昏:奶奶的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竹竿上的铁钩映着光,像在时光里轻轻一勾,就把那个不会褪色的秋天,连同满院的暖,都钩在了心上。
(黄陵煤化工:马莉)



 陕焦化工微信
陕焦化工微信